文:趙中麒
春節不是泰國的國定假日,沒有假可放。不過,今年春節剛好遇到例假日,所以,除夕跟初一都放到假了。除夕當天,跟幾位台灣來的朋友,以及一位中國籍同事,在住處附近一位當地華人A開的小店,自己動手做年夜飯,晚上就就在小店內圍爐。
在台灣,過年前大街小巷的應景歌曲、春聯,或許是身處在此氛圍中數十年,早已習慣,因此,不會覺得興奮,只覺得那是「舊年走了,新年來了」的訊息。即使是年夜飯,也只是一頓比平時豐富的大餐,而且,這份大餐每年都得吃到年初三才吃得完。博士班畢業前,連續兩年的春節在泰緬邊境進行田野研究,生活作息完全按照克倫族的行事曆進行。雖然美索鎮的老華僑都會邀請我去他家一起吃年夜飯,但心中並沒有過年的期待。不過,今年春節不一樣。除夕前三星期,就開始期待春節的到來。這是一種很奇怪的轉變。以往不太在乎的「文化」與「意義」,在今年卻特別重要。或許是長時間地忽略,以及為了田野研究順利進行,而在接觸其他文化時刻意地將自己土著化(go native),今年,在不需要這種在意識上將自己抽離於母文化的情形下,剛離開台灣四個月,便開始期待自己能夠沁淫「己文化」中,並享受在此文化中的各種意義。於是,急忙跟兩位在曼谷的台灣友人:工作的B(客家人)與讀書的C(客家人);以及同辦公室的中國籍同事D(雲南昆明人)敲定除夕一起圍爐。C則邀請她的朋友,從泰北清萊移民到台灣的泰國/華人/台灣人F。
隨著除夕的腳步愈來愈近,這種對於參與某種文化活動的期待也就愈強烈。除夕前一星期,就迫不及待地前往曼谷唐人街(Yaowarat),看看曼谷華人如何準備新年,順便拍點照片。進行典型的「族內觀光」。有許多「儀式」,是過春節必須進行的。包括「大掃除/除舊佈新」、「貼春聯」、「採買年貨與糖果」,以及「圍爐」等。這些儀式,或許進行的時間點不同,但卻共同交織成一個儀式網絡。在此儀式網絡的一方,代表一種舊有的狀態。此種狀態隱含了所有的不悅與苦楚,雖然舊有的狀態中也必然包含了美好與幸福。不過,美好與幸福,似乎被自動過濾掉,或者,自動通過儀式網絡,而與儀式網絡另一方的新狀態結合,等著我們大步迎向。儀式網絡另一方的狀態,是一種被期待的狀態。通過完成此儀式網絡中的所有活動,舊的狀態被遺留在過去,而進入另一個新的狀態。打從很久很久以前的先人們躲在家中準備好鞭炮、紅衣服以趕走年獸開始,這個新的狀態就被賦予了所有我們對美好未來的想像,而被期待著,雖然新狀態中的實際情形,並不意味不再有不悅與苦楚。或許,關於等待年獸過程中的焦慮與趕走年獸後所獲得重生的歡欣,被代代地傳述與記憶,因此,此一儀式網絡中的所有活動,便總是在焦慮與期待中,被進行著。焦慮著年貨夠不夠、春聯夠不夠、大掃除可能做不完;期待著能看到屋中大紅春聯所帶來的喜氣、期待著家人的團聚……
這種集體記憶,顯然,沒有因為海外華人離鄉背井而被淡化。唐人街中許多商家,都為了大掃除而暫停營業;有的則一面大掃除一面營業。短短約200公尺的唐人街,幾乎每五到十步,就有一個小攤,賣紅色春聯。有意思的是,唐人街中所賣的春聯,除了「春」、「福」外,其餘幾乎都跟做生意有關。數量最多的是「財源廣進」、「吉祥發財」。華人果然是愛好賺錢的民族啊。可能是因為泰國華人多數為潮州、海南跟客家後裔,所以,年貨的內容也跟台灣差不多,同樣具有中國的南方色彩:金針菇、香菇、鮑魚等均是市場中的年貨要角。不過,此處的年貨,有一樣,應該是台灣年貨大街比較少見到的,那就是魚翅。當全世界都在批評華人吃魚翅的文化,曼谷華人卻仍大張旗鼓地購買與食用魚翅。在200公尺的唐人街主要道路上,前130公尺,是以餐廳、旅館、酒店為主;後80公尺則主要是金舖。在前130公尺我所計算的20間餐館、酒店中,就有18間在販售魚翅料理。看到這一點,實在讓人感到有點汗顏。不過,到了傍晚,騎樓下的排檔開始營業,卻看到許多老外坐在排檔中享用中華美食中的高檔料理:魚翅。看他們吃得很爽的樣子,讓人不禁想上前聊聊,「魚翅好吃嗎?媽的勒,你有種批評,還吃個屁!幹!!」
在唐人街逛到一項幾乎要讓人落淚的年貨,就是青綠色長條型的冬瓜糖跟外層裹紅色或白色糖粉的花生。這兩樣糖果,是小時後每年過年都會吃的糖果。但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過年前住家附近賣糖果的商店已經不賣了,也吃不到了。坦白說,這兩樣糖果,並不好吃。小時後,每年都只吃幾顆應景而已。可是,或許是因為人在異鄉,所以,即使是不好吃的東西,也突然可以讓人差一點熱淚盈框。看到這兩樣糖果,立刻買了一包。要價50。雖說不便宜,但為了自己的熱淚,還是值得。
接近過年的時候,台灣大街小巷都是過年的應景歌曲。然而,唐人街中的小販、商家所放的應景歌曲,卻不是我們平時所熟悉的「鼕鼕鼕鼕搶」、「新年好」。好不容易聽到一首曾經聽過的歌曲,卻讓我的熱淚再也控制不住地嘩啦嘩啦流。歌名不記得了,歌詞是:「梅蘭梅蘭我愛妳……」這……應該是群星會時期的歌曲吧?聽到這首歌,我們的父母輩才會聽而現在早已沒有人哼唱的歌,在唐人街被用揚聲器放給每一位路人聽,怎不叫人感傷。雖然路人也聽不懂。
除夕前三天,另一位朋友E(小老廣),從台灣來曼谷度假,便想當然地成為我們圍爐的一份子。除夕當天,C、我,以及E下午就到A老闆的店中準備晚上的年夜飯。前一天,特別請A老闆幫忙訂餃子皮跟餡,準備大展我山東人的長才:包水餃。可是,除夕當天下午,到店裡看到的卻是餛飩皮。前一星期在唐人街,看到一間遼寧餃子館,原本想去吃點水餃,可是,我不吃豬肉,而傳統的水餃是以豬肉為餡,所以,我選擇去另一間華人小館吃水餃。當時,看到菜單上的菜名標示著「餛飩(水餃)」。原來這邊的華人把餛飩跟水餃當成同樣的食物。所以,12日,訂水餃皮當天,還很害怕老闆會弄錯。可是,老闆在年輕時曾回中國讀書,應該能夠分辨,所以,也就沒有叮嚀。結果,除夕當天看到的還是餛飩皮。這下慘了,山東人會包水餃,但不見得會包餛飩。而且那個餛飩皮,是廣東皮,也就是黃色的皮,比起我們一般所用的皮,更沒有延展性,也更容易破。E是個小老廣,看到黃色的皮,就很興奮,立馬說她知道怎麼包廣東餛飩。好吧,那就讓她包吧。我呢,則繼續堅持山東人的原則,「包水餃」。我想,以我博士的智慧,應該可以成功地用餛飩皮包水餃。
除了水餃/餛飩,C貢獻了鳳梨蝦球、蓮子湯;D貢獻了白菜雞湯跟炸魚;我則另外炒了高麗菜。就這樣,七手八腳,弄了滿滿一桌年夜飯,其中,水餃/餛飩就有四盤;高麗菜有三盤……開動時,發現A老闆的太太不知道從何吃起。原來,我們準備的菜,不酸、不甜、不辣,不符合泰國人的口味。即是連水餃/餛飩,都不知道怎麼吃。因為,在泰國,餛飩是與麵一起煮的。對他們來說,餛飩一定要有湯才好吃,沒有湯,他們就不知道怎麼吃。但我們有白菜雞湯,把餛飩丟到白菜雞湯中就可以了,這位老闆娘卻仍然動也不動。我相信,不是難吃的原因,因為我們幾個非泰國的華人都吃得很高興。
我們幾個台灣人,相似的生活背景跟語言模式/內容,所以,很容易找到共同的話題。尤其是聊到跟台灣有關的話題時。此外,因為這些朋友們不熟悉D,也不知道什麼對D來說是敏感的話題。另一方面,D比較想看中央台的春晚,所以,大夥兒跟D似乎不太有火花,除了王菲以外。因為,根據B的說法,王菲是兩岸年輕人的共同話題,雖然B其實已經不年輕了,哈哈!A老闆則因為其泰國籍的背景,更不容易切入我們的聊天內容。後來,B問了A老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當下讓所有不同族群/國籍背景的Chinese有了共同的話題:「老闆,您為什麼會到泰國來?」A老闆是在泰國出生的第二代華人。他父親在泰國賺到錢後,於晚年選擇回中國定居。A老闆則跟著「回去」唸書。在中國,A經歷了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大躍進時期的苦難,甚至曾經是紅衛兵,最後終於決定「回到」泰國定居。B曾在台灣的NGO工作,後來發現該組織的國際侷限,一方面也想了解國際NGO的運作,而到曼谷朱拉隆功大學攻讀國際發碩士,隨後在曼谷定居。C想攻讀考古/博物館方面的碩士,先至曼谷政法大學選讀泰國研究(Thai Studies)。初抵曼谷便體會台灣社會的視野狹小。曾經喜歡曼谷甚過台北,但卻又發現曼谷國際化之扭曲,而開始對曼谷感到不耐。我則因為對台灣的身分政治感到無奈又無力,選擇到沒有這種紛擾的地區工作。E為了避免陷在台灣與中國的意義紛爭中,決定在這個原本屬於Chinese的節日離開住著Chinese的土地。F的背景,太過複雜,恕小弟腦力有限,無法簡述。如果diaspora的第一層意義,是遠離家鄉,而在異鄉面臨著、經驗著對家鄉與異鄉的衝突認知,哪麼,我們都符合這種第一層的diaspora意義。於是,年夜飯的後半段時間,就成為幾個自願成為diaspora的年輕Chinese對泰國老Chinese的diaspora、歸鄉與生根經驗的見證會。只是,不知道過了除夕後,這位繼承了華人千年集體記憶與數十年個人流離與生根經驗的老Chinese,對於穿越儀式網絡後的新狀態的想像與期待是什麼。
在除夕來臨之前,愈接近除夕,我的心就愈亢奮。一種帶有期待的亢奮。期待什麼?年紀這麼大,已經沒有紅包可以領。除夕的年夜飯夥伴,其實在平時也可以約出來吃大餐。孤身一人在曼谷,工作沒有想像中如意,朋友也不多。那麼,期待什麼?除夕當天上午,一起床,就迫不及待地整理房間,貼春聯,而這些活兒,是以往在台灣時所不喜歡做的事情。在台灣時,每年到了大掃除、貼春聯的時後,都得老父三催四請,才能叫動我去完成這些過年前必須完成的儀式。然而,今年,離開台灣後,卻又急迫地想去做這些事情。在房間門口貼上春聯,讓所有人知道,我是個Chinese......
在唐人街,看到眾多的Chinese準備著過年,雖然我們講的語言不同;在A老闆家,來自四方不同國籍與族群背景的Chinese一起圍爐吃年夜飯。不同地方的Chinese,在春節這個時刻,透過「春節」這個對Chinese來說最具有文化與歷史意義的節日,透過參與儀式網絡中的某個儀式活動,彼此間有了一種似乎早已存在多年的默契與了解。這是千年來的集體記憶嗎?
後記:
本文所用的「中國」,有指當前政治意義的中國,也有指文化與歷史的集體連續。但Chinese則是一種文化的指稱。在當前台灣的環境中,許多人對此二字敏感。若你/妳/您敏感,請自行迴避。你/妳/您可以不同意我將中國,Chinese與春節連結,但這篇報告,在某程度上,是本人對過往生命經驗的反思,請尊重。如果仍想針對什麼是中國,什麼是Chinese這種事情放炮,請自便,但我會視這種「炮」如瘋狗吠月而不理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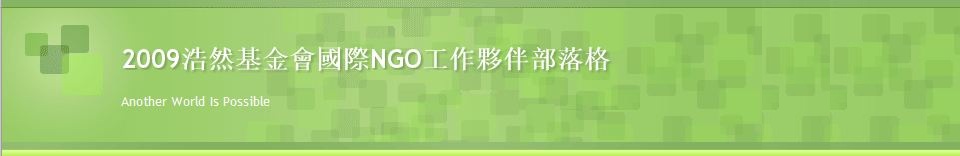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9 意見:
那到底用餛飩皮包水餃有沒有成功?
很神奇的是,那個黃色餛飩皮,包的時候,餡不能弄太多,不然容易就破掉。可是,下水煮,卻不會把皮煮破,反而很有彈性。尤其是,下鍋後,整鍋水都被染成黃色......不曉得是色素還是啥原因....
那你要不要檢查一下餛飩皮是不是內地來的。
看了不知道為何很感動,尤其是 「魚翅好吃嗎?媽的勒,你有種批評,還吃個屁!幹!!」
喔不對, 最感動的是早上起來貼春聯的故事,博士真可愛
哦哦,這篇文在facebook 被貼了9次耶。
扭曲國的國際話那篇被分享31次耶,所以9次算多嗎?
原來博士的文章可比洛陽紙貴,這麼多人爭相轉寄。
喔,原來我的文章洛陽紙貴?那應該開始寫點能賺錢的東西了,是吧?
是啊,可以開始考慮寫文章維生。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