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們的研究人員們,在IPF聖保羅辦公室,全職人員約六十至七十位。
以教育項目區分為大眾教育、成人教育、公民教育,其中工作人員大多為與政府合作或特定專案經費底下的約聘人員,並不算是IPF自己的研究人員。隨專案計畫來去,也不是每天朝九晚五地待在辦公室。
研究人員之外,專職在IPF工作的人員還有財務人員、網管人員、通訊人員、部門主管。除了部門主管,其他專職人員的工作就像是與其他所有企業組織,公司行號裡的人員相同,只是對象換成Paulo Freire研究機構。
而一個文化迥異,語言不通的國度前來的「交換計畫參與者」,扮演的角色則是在這個教育研究當中,跨國界、跨文化連結的樣本。
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執行組織在地行動的NGO針對一地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然一個問題發生的背景往往是牽涉全球,牽涉各種層面,各色人群。
NGO實際進行的工作是對站在不同的地點,不同文化脈絡上的不同人群提出組織,而非針對問題做出改變。一句在IPF聽來的老話︰「我們並不能改變問題,但我們能教育有力量改變這個世界的人群。」
我們被分派到的教育專案,於是乎是公民教育項目當中的「行星公民教育計畫」。 這個教育計畫在聖保羅旁的衛星都市Osasco進行,由IPF,Osasco政府以及一所公立小學合作。 其提倡的行星公民教育理念便是一個跨文化永續責任的核心概念,卻同時重視不同個人和不同文化經驗所激發出的不同實踐。 我還尚不能理解自己所能做出的付出為何?也許一個來自不同文化的思考和見解,聽起來很新鮮,很有趣,但對於在地的行動有何幫助?
接下來的工作成為撰寫報告以及針對開會討論,閱讀文本,看影片。 甚至每一個小小的討論,都必須上呈報告。 我開始想,這些我們的回饋,是如何加入IPF對於教育研究與實踐工作的運轉齒輪。
當時在Osasco的工作坊,我們討論在Osasco發生的水資源議題過程時,我開始思索,同樣的問題是以怎樣的形式發生在我在台灣的生命經驗當中,是如何被我們處理,被面對。 而在此地,又是如何被看待? 一個小學生對於水資源保護的最基礎認知是「我不要丟垃圾在河川中」。 當我是一個小學生時,我的認知又是為何? 突然間已經在我腦袋裏面沉積已久的記憶又開始攪動了起來。
我們在地圖上標誌每個人的來處,遍佈在這個星球上的各洲。
 這是個簡單(且老套)的小活動,卻給了我一個不同以往的啟發。 首先是,了解自我。我們從他人的投射中發現自己未曾發現的自我,省思被自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物是如何特別,這些是在何種脈絡下以這樣的形式產生? 工作夥伴在異地給組織和自我帶來的種種不同的問題和挑戰,確實是給予一個組織更深度了解本身所處背景的契機。而我們所能提供的回饋,對於一個在地的行動來說,是一個以不同角度投射自我的鏡子。
這是個簡單(且老套)的小活動,卻給了我一個不同以往的啟發。 首先是,了解自我。我們從他人的投射中發現自己未曾發現的自我,省思被自己當作理所當然的事物是如何特別,這些是在何種脈絡下以這樣的形式產生? 工作夥伴在異地給組織和自我帶來的種種不同的問題和挑戰,確實是給予一個組織更深度了解本身所處背景的契機。而我們所能提供的回饋,對於一個在地的行動來說,是一個以不同角度投射自我的鏡子。
所以國際交流的意義為何? 在自己訪問幾位從事環境運動的各國青年不多的樣本數當中,不約而同的,許多青年都從「組織網絡(networking)」開始一個行動。當時的我心想:「啊不就是想要到處認識朋友到處玩,social就social啊組織網絡聽起來比較高級喔?」 之後了解到,網絡,除了是組織力量取得發聲權和影響力。更是「跨越」。 從跨越自我本身,到跨越背景及文化差異的組合,異中求同,同中見異。使在地行動同時兼具對於問題深度及廣度的跨越。
同樣的理念,如何在不同的研究機構,不同的人群當中用不同的方式解讀與被實踐,研究他人同時是研究自我的歷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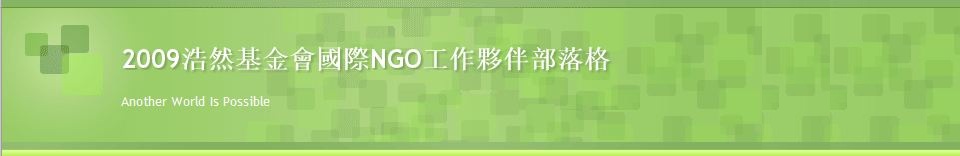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