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楊淑華
三月,進入泰國的熱季。按傳統,泰國分成三個季節,熱季、雨季、涼季,不過處在中部地區的我來說,除了涼季時洗那冰涼的洗澡水時感到透心涼外,大概就像是大家開玩笑的,現在的中部泰國三個季節是,熱、很熱、非常熱。而原本頭髮就不長的狀態下,又把頭髮剪得更短了,期待在勞動工作後享受那一舀水從頭沖到腳的暢快。
這個月開始沒多久,就處在移動中的狀態。先是兩天三夜的清邁行,其中兩夜睡在火車上,接著是單日的市區及曼谷行程,然後接著又是十幾天的農家住宿,在四個不同的農家間移動,中間又因為辦理簽證回辦公室及到大城一趟。總之就是在不停的適應不同的生活環境及準備行囊的狀態中,有很多的學習,但是也累績著不少的疲憊。
很多的事情在發生,很多的學習需要沉澱再思考,很多的生活瑣事好玩的、不開心的想要紀錄,很多的接下來的後續想要規劃,但是在這段時間都很難達成,像是被行程追著跑般的一個接著一個,滾成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渾球。
而最容易書寫的當然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插秧,而這六個月來也顯示著:我跟這個工作很有緣份,總是能迎接到大部分的插秧時刻。這個禮拜有些不同,以往插秧的地都是在辦公室外面的那三塊地,和KKF的worker一同進行,而這次則是在另一塊車程不到十分鐘的外邊地插秧,和從社區請來的婦女插秧大隊一同工作。
(秧苗育種在辦公室外的地,插秧前須另有人力取秧苗)
聽聞有這塊地好一陣子,倒是第一次接觸,沒想到一下子就有那麼深的關係。地總共八萊,也就是一甲三分多,看到一下子要手工插秧這麼一大片地,還真的有點腳軟,如果按照之前使用12株苗的拉線,四五個人力,那真的是要做到地老天荒。而這次主要的人力來自於KKF其中一個農夫學校的社區裡的婆婆媽媽們,大概十二、三人。
拉線一拉就是七八十公尺,工人一字排開,手中抱著秧苗開始左右移動的插起秧來,平均大概一個人一行十二三株秧苗。當然,每次開始也是在跟你兩旁的人培養工作默契以及找出最佳距離,畢竟大家快慢不同,需要拿新秧苗的時間也不一樣,適度的調整距離才能讓整理工作速度加快。
工作時間大概是早上七點時,辦公室職員開車到社區去接農民到田裡,上下午大概各會有一至兩次的休息,端看耕種的秧苗多寡。而辦公室這邊則是準備飲料茶水,和一些點心給大家吃,工作到下午五點左右。中午則是大家各自準備米飯,和帶一道菜一同食用。
在泰國不管男女我遇到的通常都飯量驚人,可能是我接觸的大多是勞動者吧(都市小姐可能有不一樣),以往在台灣我一碗飯或便當裡的飯吃光光在女性同胞中已經算是屬一屬二,但在這裡一盤飯大概可等於1.5~2碗的飯量(但是在外面賣的飯倒是份量都小小的),而不少人都還會再添第二盤。以往我不太理解泰國為何是米食大國,台灣也吃米啊,現在我很清楚「差遠了」!在這裡從早餐開始就煮米,三餐吃米飯是常態,而且量又多。而我在這兩天的午餐時間也的確看到大家帶了滿滿一盒飯的餐盒,配菜量反而不多,有的人只是帶了一小盒的辣椒醬(泰國有各種不同的辣椒製醬料),就可配著飯吃。
在田裡工作一整天,吃喝拉撒當然也都是在田邊進行。中午躺在樹影下休息,並沒有清涼的感覺,炙熱的天氣讓地裡冒出陣陣的熱氣,躺著只是覺得可以換邊烤均衡一下,讓原本彎腰只黑背部,反過來曬一曬正面。而中午過後下田,水可燙腳,原本擔心腳上的傷口下田會不會惡化感染,但是想想每天太陽耗費他那麼多能量放熱消毒,到也安心了不少。
剛到泰國時,面對到處都是冰塊水的飲水狀況頗為擔心,因為從小媽媽就教育「吃冰的不好」。雖然我不是什麼乖小孩,一樣都有在吃冰,但是也沒有到那種任何時刻都是喝冰水的狀態。所以以往下田工作大多是帶著自己的瓶子先把冰水裝進,等到稍微退冰。而其實也因為炎熱季節的到來,也越來越常直接飲用那超冰涼的水,邊喝還不免擔心:慘了慘了,下次生理期來要痛死了。但是現下的痛快還是先把握住了!
而這次因為工作在外補水不易,所以當然也就跟著大家拿共飲的水杯,舀那保溫桶裡的冰塊水喝。也因為是伸杯子舀水,而水杯在外面接受各種雜質,所以慢慢地水裡就漂著一些小東西。那是喝的水,而清洗是用田裡的泥水,還不像台灣有水圳的水,而想想一開始在台灣種田,還擔心著水圳的水乾不乾淨之類的。在這裡的農業生活也一再的挑戰過往教育給我的衛生、乾淨的概念。
勞動一天後,在收工前負責的職員總會買來最後一種特別的飲料—米酒給大家。那是一種熟悉的氣氛,雖然在台灣的時候我多是飲黑色的飲料,米酒比較像是男人的飲料,不過當農人倒了三分之ㄧ咖啡杯遞給我的時候,就像是在布農族的部落裡,大家共用一個杯子飲酒的氣氛一樣,為了不耽誤下一位,一口氣就乾掉,也贏得農民的喝彩@@。沒想到在回程的路上,覺得世界有天旋地轉的感覺,詫異了一下:奇怪,又沒有喝很多啊!後來友人告知才知道那米酒的濃度有40%以上,哇!台灣米酒頭濃度有這樣高嗎?原來是高梁等級的!
農工工作一天的收入是200元,這可以知道為什麼泰國人會到台灣工作,而台灣人只會到泰國渡假不會到泰國工作(除非是跨國公司之類的),也痛心我這樣要死要活的工作一天價值竟然是如此的低廉。就像這週二晚上農民訓練課程所看的節目影片所看,農民即使再勤勞再怎麼不偷懶他們的生活卻總是處於清貧的狀態,開始想著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文化倫理,讓我們可以這樣接受為所有人生產糧食的這群人過著比其他人還要辛苦的生活?
(工作後最好的飲料,來一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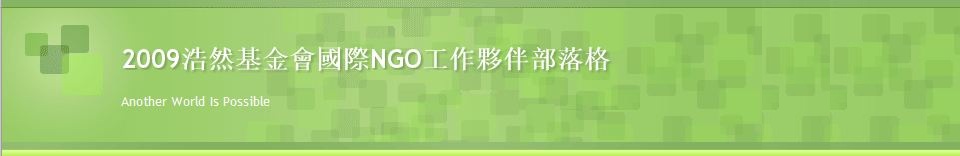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2 意見:
淑華, 我真佩服你。KKF的工作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咧。有機會也想體驗農家的勞動耕種生活。
泰國的插秧方式真的跟台灣很不一樣,以前人力插秧是先把水放掉之後,再牽輪仔,在田裡畫出一格一格的格子,秧苗就插在交叉點上,秧苗也不一樣,是一片片的憑經驗以手指信手拈來往地裡裁,沒有時間去屬多少株,一個人一次可以插五行,秧苗就放在秧盆內,腳跨兩行,右邊二行,左邊一行,以利推盆,小時候先前行,再慢慢學會倒退嚕。高手不用牽輪仔畫格子也可以插得又直又整齊。
牽線看來真的速度一定會慢很多,在台灣插秧最厲害的是女人,我們都稱下港班仔,包巾蒙面,速度快得驚人,應該都是從南部來的,小時候從未見過她們的容顏。
至於米酒,台灣有四十度的米酒,是農民自己私釀的,以前在台中就喝過,用四加侖的桶子裝的,蒸餾過,跟高粱差不多。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