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陳婉寧(北京自然之友志願者)
前言:
一月底至二月份摻雜幾件性質不同的工作內容,在此期間自然之友內部也進行了為期四天三夜的團隊建設,也是我第一次參加NGO內部集訓,在台灣能力建設對NGO而言似乎是不太受重視的一塊,不論是在台灣的NGO擔任志工或兼職人員,全年都是忙得焦頭爛額,哪還擠得出時間做團隊建設規劃?!其次,二月份較多時間投入教育活動部之協作,規劃年度的自然體驗項目及自然體驗培訓師課程,也藉由幾次實際參與活動項目瞭解活動對象及未來改革思路;第三則是延續過去幾個月在北京加入「一人一故事」團體的基礎,再加上向外擴展進入打工子弟學校服務的機會,透過戲劇的工具手法找出群體力量與結合組織環境教育項目的切入點。
劍拔孥張的和平
2010年新的開始,自然之友內部期待在未來的組織路上都能夠有定期的團隊建設,俾便交流組織內部情感與工作上脫開辦公室關係的溝通。其中由德籍專家博盟先生為大家規劃關於組織文化、個人特質與組織思路策略一項最為受益。恰巧博盟先生引領的幾個團體集思方法透過遊戲、圖畫及交互討論貫穿,整個討論的氛圍正因為脫離固有的辦公室空間,權力關係與公事文件,大夥顯得更容易卸下「另一張臉」、很多內心對於組織進行的方向、組織內部隱隱然的團塊關係、更感性傾訴的一面、對事情或對個人的看法描述…等,都或多或少地彰顯在這一條難得浮現的交叉線上。平時的組織內部愉快平和,就是博盟所謂的「客氣話」,而在長久的客氣話後,累積的到底是越來越多的「對不準」還是真正的理解?客氣、和平與團結,不見得是我們需要的組織文化,其也不必然代表全然的正向。在經過一天馬拉松式的「組織大解剖」,同在一艘船上的工作同仁,解讀我們正在搭的這艘船的形體、功能、航行方向與該補強處截然不同,即便我們的目標一致,卻也東拖西拉緩慢前進,這些結果透過有趣的小遊戲體驗出來的具象差異極其驚人;工作人員的個人特質分佈與對組織過去、現在、未來的心內感受說明像抽絲剝繭似地讓性格與情感的矛盾針鋒相對,有人認為得不到應有的組織內部支持、有人感到組織文化移轉的焦慮,一瞬間如炮竹點燃地剎那聲火齊放爆出,好似累積了一年的能量般釋放;當下的感受很是複雜,一是這樣的情緒爆發是與辦公室的平和輕鬆相互錯置的,二是原來我們都生活在某一種可接受的情緒膜層之下,在其中與組織互動,卻未必是能夠更精準地表示自己的情緒與需要,當然也不容易得到適切的回應;三是任何NGO的組織管理難度都絕不亞於所謂的資本企業,越往博盟專家設計的遊戲走,越可以發現與「人」有關的一切都不簡單,人在組織內角色的隱藏顯露,那個人與人之間力量的拉扯消長是很浮動有機的,就好像很多原子在裡面衝來撞去,而不同性格的原子間需要相互制衡,哪一方多了就容易朝哪一方去,也太過單向。
有激動、有淚水、有歡樂、有嚴肅的香山團隊建設最終在難得的北京高溫中落幕,車窗內外都一片暖黃歡快,窗景外唰唰而過的樹影山巒,也唰唰地把我們收進城市…。
老師,你看到了嗎?對環境的知與無知
過年前的日子正忙碌幾個兒童冬令營的協作與學習,同時展開招訓日後做為自然體驗培訓師之課程。簡單來說,自然之友開展環境教育項目已行之有年,早期致力於環境教育於城鄉間,也漸步培養大學生前往協助偏遠省分之環境教學,也有「羚羊車」滿載著教具、教材與老師、志願者上山下海至需要之處進行教學。而環境教育也是許多其他環境組織著力的面向,只是大家關注的受教對象、使用傳遞環境教育之工具手段不一樣。目前自然之友對環境教育項目的策劃正在漸步思考轉型,也算是亦步亦趨地開拓前進道路。手邊負責的培訓課程也將投入後續轉型中的環境教育。
自然體驗培訓課程的設計對我而言是相對容易,因為過去在台灣類似的經驗尚可參照;但與小孩長期相處的經驗則相對缺乏,剛帶兒童營的幾天就被精力旺盛的小夥子們嚇到,搞得疲憊不堪!但也透過與孩童相處互動的經驗得到一些觀察。同時自己也並非教育專業人士,剛好這是一個讓我惡補教育哲學的機會。也因為開始關注教育,「自然體驗」、「自然教育」的定義,對我而言不是那樣地狹隘,顧名思義,大家或許覺得就是將人帶入自然環境走看,體驗分享與學習。這樣的教學模式是最常見的,也很容易就可以落筆為教案書寫;只是幾個小時下來,孩童真正累積到了什麼?是表面的還是深植人心的?「垃圾分類」、「資源回收」、「不使用一次性產品」、「愛護自然」、「節約用水」…這些詞彙的意義在哪裡?是不是這些用法與解釋的範圍都被固化在活動中而已,離開活動,很多家庭父母或孩童自己的行為其實背道而馳。這些環境背後的教育哲學要怎麼被挖掘出來?又如何去傳達?而自然教育和其他教育領域的類別就像一個同心圓般,由數個不同教育領域的圓疊合起來:當我們帶領孩子走向戶外,自然知識系統綑綁的束縛應該降至最低,不管是泥土、石頭、動物、植物、流水、雨滴、風聲與日曬,環境元素所構成的空間場域是提供很多生命與當地人文歷史線索的架接,一些生物交配的傳承、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現實、各種資源分配的均與不均…等,都是提供環境教育的支撐。這些支撐需要師者引導、打開與發現這樣的哲學──不論身在哪一場合。
在幾次兒童營用餐時,個個都是父母心頭肉的獨生子女,不乏有一邊吃一邊嫌:「這個飯好難吃」、「我不想吃」、「這個我不要」、「我想吃別的零食」…等,雖看似環境教育無關,我看在眼裡,卻直接聯想到在北京其他地區的孩童未必能享用對等的社會資源、教育資源,或是全球糧食與水資源的分配不均。師者的知與無知,是不是該在這個時候相互決鬥一番?!知的是你有能力(也有義務)機會教育引導大環境資源不公、跨國環境資源掠奪之議題,(而這些對環境問題馬上舉手搶答標準答案小朋友們,離開「教育場合」,馬上原形畢露…);無知的是師者看不見也無感於型塑生命教育的契機。
環境教育的內容層次、廣度和教育模式,台灣與中國間還是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差異性。我有幸可以參與其中,並且有實際場域能夠滲透式地提出想法、執行計畫,很多都屬實驗性質的階段,還不知道會冒出怎樣的火花,帶來一點擾動、帶來一點歧異與環境公民的力量。
兒童 × 戲劇 × 環境 = ?
延續前述所提在城市中辦理的兒童自然體驗營隊,自然之友另外的環境教育目標是透過收費之自然體驗營盈餘所得提供京城近郊資源相對薄弱的打工子弟小學也能享受到一樣的教育資源。基於過去與其他NGO人士運作了幾個月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恰巧也有機會在本年度進入校園進行為期一學期的戲劇帶領。我想透過戲劇的媒介瞭解更多關於該地打工子弟小學的社會狀況、地方情事、階段性孩童的各種需求、心理狀態與對社會環境(或自然環境)的感知,同時與孩童地方環境認同的滋長培養是同步鑲嵌進行的;進行城鄉結合部環境教育項目的第一步在我的想法中,不是去急推項目的執行,應該是回過頭來瞭解對象,看到城鄉間環境教育的需求差異、執行差異、認知差異與教學差異,從戲劇中去聽到聲音、看到人物與瞭解故事,讓人物去串連人物;這些工作可以深耕而長久地持續,再慢慢型塑改善城鄉結合部環境教育的方法手段。這幾日有會機與幾位同是志願者再度複習幾個基本戲劇環節及遊戲,最後一日大家則瘋狂「飆戲」,簡直是演上癮了!身體、四肢、情緒、表情及聲音被一點一滴地釋放流洩。
面對未來幾個月兒童 × 戲劇 × 環境 = ?的挑戰,我簡直躍躍欲試!搭兒童的台、唱兒童的戲、教兒童的育!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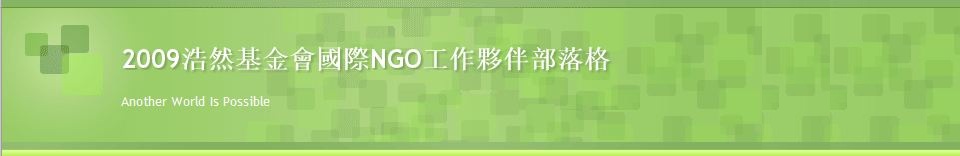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JPG)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