寬恕與正義
文/趙中麒
一月8日與9日兩天,在朱拉隆功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Social Research Institute, Chulalongkorn)會議室,有一場關於公民社會與正義的工作坊。工作坊名稱為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lobal Civil Society。此工作坊的舉辦單位為印度孟買的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泰國朱拉隆功大學,以及倫敦政經學院全球治理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LSE)。朱大的和平與衝突研究中心(Centre for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Chulalongkorn)則為承辦單位。
參與此工作坊者,多數為在亞洲地區從事相關研究的學者以及社運人士。之所以舉辦此工作坊的原因在於,全球治理的時代,原本在特定國家疆界內行動的市民社會組織,也需要跨越國家疆界,以交流彼此經驗,與建立彼此的聯繫。正義與公民社會,是一個跨越國家、文化、種族、地區等的普世概念。然而,正義之實現,以及鞏固公民社會以培養社會力,則有賴於不同文化、國家與種族等對其之理解。如何在普世與在地之間尋求中道,以公民社會為媒介來實現正義,就是這個工作坊的目的之一。此工作坊的第二個目的,是希望透過學術界與公民社會中的行動者彼此間的討論與激盪,以明晰對亞洲來說最為關鍵的正義概念與公民社會的行動策略等。關於這兩項目的,我們可以從工作坊的議程安排看出來。有意思的是,工作坊結束後,主辦單位希望刊行全球公民社會年鑑(Global Civil Society Yearbook)。在此年鑑中,經由簡單的分析,以提供亞洲地區較為關鍵的相關議題之圖像。雖然不知道此年鑑何時出刊,但似乎是一個相當具有企圖心與遠見的做為。
工作坊第一天的議程,是在抽象層次討論「正義」與「公民社會」等概念。不論我們願不願意承認,關於「正義」與「公民社會」概念的起源與意義(事實上,包括民主、人權等也是),多是在西方的脈絡下進行的。關於正義,有學者追溯其概念源於洛克的社會契約論、有論者認為正義概念的起源,應溯至柏拉圖理想國的政治設計;關於公民社會,將其視為西方資本主義發展至某個程度後所發展出來的結社藝術,則幾乎已成為定論,因此,關於中國等未經歷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國家是否有公民社會的爭論才會不斷地上演。事實上,正義與公民社會,均為一種具有普世性的概念,可以在任何地方發現,也可以在任何文化中被辯論。只是,因為大部分的思辯是西方學術界在西方的脈絡中進行,因此,一個原本普世的概念在非西方社會是否能夠應用,如何應用,便成為值得討論的議題。在第一天的議程中,首先上場的主題,就是西方的正義理論是否能應用於非西方社會,以及公民社會、正義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第一天議程的報告人,無一例外,均來自於學術界。
第二天的議程,則聚焦於如何經由bottom-up的途徑,實現正義。報告人,則包括了積極投入社運界的學院人士,以及亞洲地區的公民社會團體負責人。
第一天的議程,羅爾斯(John Rawls)那艱深難懂的正義論幾乎被每一位報告人所引用。因此,不意外,第一天的議程幾乎變成學院人士的討論會。第二天的上午,則變成民間團體的天下,因為報告內容,都是各團體在各自的田野地所進行的運動,例如Living Rivers Siam報告其在Salween River所倡議的反水庫運動、Mekong Program on Water Environment and Resilience在湄公河流域針對土地與糧食主權所進行的調查報告等。根據觀察,除了那些積極參與社運的學者,其餘學者幾乎無法對民間團體的報告進行任何評論或給予任何意見。因為,他們中的多數,習慣於翱翔天際,早已忘卻如何用雙腳在充滿泥濘的森林中行走,相反,民間團體則需鎮日於森林中迎戰窮凶惡極之獸,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亦步亦趨地跟隨學院中的祥鶴翱翔於天際。
比較有意思的是,第二天最後一個panel引起了學院人士與社運人士的共同興趣。主題是正義與寬恕(Justice and Forgiveness)。報告人指出,受迫害者,可以選擇用報復的方式,來回復他所認為的正義,但是,他最後選擇寬恕加害人。因此,報告人認為,寬恕的本身,是一種價值的選擇。不過,這種價值的選擇,不應該附帶任何條件。報告人的觀點來自於她在中國的經驗。由於日本於二次大戰期間在中國犯下的罪行,使得多數中國人對日本仍抱有強烈的敵意。然而,一位中國女孩,曾寫一篇文章,要她的同胞放下仇恨,寬恕日本的戰行,因為,歷史已經發生,無法改變。報告人因此感到訝異,而以此為例,告訴我們,寬恕是一種無條件的價值選擇。
寬恕的本身,是一種價值選擇,無庸置疑。但是否應該是一種無條件的價值選擇,則不無疑問。的確,如同南非大主教屠圖所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No forgiveness, no future)。可是,面對集體的創傷,寬恕便需附帶條件了。
以日本侵華為例,多數中國人對日本仍抱有敵意,部分原因當然在於日本於侵華時期犯下許多違反人道的戰行。但主要原因在於,至目前為止,日本仍不願承認其曾犯下的戰行,即使無數證據足以證明,其甚至不願承認他們對中國所發動的戰爭是侵略。對於中國人來說,日本侵華所造成的是一種集體的創傷,而日本不願承認其對中國的所作所為,則意味其不承認對中國的集體創傷需負擔任何責任。因而,對中國人來說,其所期待的正義,將因為沒有承擔責任者,而無法被回復。
這種集體創傷,也可以在其他地方發現。例如,因為軍事政府的政策,所造成緬甸境內各少數民族與緬族之間的仇恨、因為國民黨白色恐怖所造成台灣本省與外省族群間的對立、中國漢族與維吾爾族之間近乎無解的民族衝突等。即使對立群體間的個人,可以理解彼此之間的對立原因,但這種理解,無法化解兩個群體之間的衝突。換言之,集體創傷,無法透過對個體的心理慰藉,而被治療。因為,即使我的創傷不再,但我的父母、親朋好友的創傷仍存在,整個社會仍處於創痛期。對此創傷的療癒方式,需要以集體的方式為之。一種方式,就是加害人必須承認他們對受害人所做的行為,告訴受害人當時的真相。
的確,即使告知真相,也不代表受害人將會就此寬恕加害人。重點在於,作為受害人,群體將會知道一個事實,以及誰需為此負責的對象。那麼,受害群體可以選擇他們願不願意寬恕加害者。兩個群體之間的仇恨也將有機會化解。
總之,無寬恕,就沒有未來,但面對集體創傷,要求寬恕的條件,就是事實。唯有事實被忠實地呈現與承認,集體創傷,才有可能獲得療癒,正義也才能被回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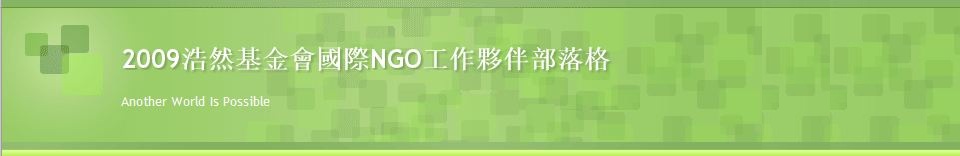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3 意見:
參加的學者大概有"Ashwani Kumar"、"Jan Aart Scholte"之類的吧?如果有,分享一篇在OpenDemocracy的文章。關於全球公民社會、貧窮、行動。
http://www.opendemocracy.net/article/poverty-and-activism-the-heart-of-global-civil-society
"根據觀察,除了那些積極參與社運的學者,其餘學者幾乎無法對民間團體的報告進行任何評論或給予任何意見。因為,他們中的多數,習慣於翱翔天際,早已忘卻如何用雙腳在充滿泥濘的森林中行走,相反,民間團體則需鎮日於森林中迎戰窮凶惡極之獸,他們沒有時間與精力亦步亦趨地跟隨學院中的祥鶴翱翔於天際。"
非常有趣的觀察.請問飛鷹(flying eagle)趙博士,您是翱翔於天際,還是也能直撲而下迎戰兇惡之獸?
我是不問紅塵俗事的比丘老鷹。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