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米之神体验之三
----------农民在农具方面的创造性体现
图文:袁清华
人类最伟大的品质之一便是创造性--------莫里斯
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水稻的收割和蔬菜田的翻地、除草工作。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时,看见这里的农民拿着松动的锄头,找来木块和斧头,没多久就做出一个大小合适的木楔,娴熟的将其塞了进去,松动的锄头顿时变的牢固无比,不禁感叹农民的智慧。而现在,农民在实际生产中掌握的技术和创造的工具却在工业化的强蚀下渐渐消失,伴随着农具消失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更是一种文化。
记得小时候,不是所有农家都有各种工具,所以有时劳动就会去街坊四邻借农具。镢、锄、犁、扁担、耧子、镰刀经常可见,等到归还时即使同样的农具也可以很容易的分辨出来,因为每家人使用习惯或选择材质不同,在每件农具上都会有不同的使用痕迹。因此,以前的农具都和农民有着很深的感情,农民过去称农具为“家伙事儿”或“家伙”,可见其亲密程度。

当从远古的石器、青铜、铁器发展到现代的农业机械,现代农业生产中无论是农民主动接受还是被动选择,毫无疑问的是现代机械已经占据了大部分农业的生产,而那些传统农具也好像完成使命一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或是灰飞烟尽,或是被放置在博物馆内。

首先,应该承认,农民因为生活在实际生产中,最能体会劳动工具的适用性,因此会根据个人能力、地域区分、作物区别等生产出相应的工具,并不断被后人完善。所以这些工具都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过的,具有很强的推广性。
其次,农民的创造主要考虑生产的适用性和成本,又由于其掌握的资源有限,因此尽量选用本地、方便的材料制作,无论在能源消耗上还是环境污染上都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
第三,农民创造的工具基本属于个人所有,受外界社会力量支配有限,农民可以最大程度的自由使用。
第四,创造农具的技术可以通过传授和练习获得,具有非常大的学习空间。
当我们被巨大的蒸汽机带入工业化进程中,我们基本能想到的各种工具被生产出来,虽然里面也体现了一部分人的智慧和创造力。但我们(尤其是农民)能否像过去一样方便自由的使用吗?
我们尝试着做些比较:首先,工业产品中(重点指农业生产、加工工具),产品的创造和研发成为少数人的智慧体现,为了追求最大化利益,试验的时间被缩短、试验的范围被缩小,这些都意味着产品可能存在适用性方面的缺陷。
其次,大部分产品被标准化、统一生产。差异化体现基本消失,即使一个产品会有多个系列出现,其实也针对的是不同群体人员(主要从经济收入或地理区域等方面考虑),基本不会为个人使用的习惯与感受而考虑。
第三,现代农具中,产品多以塑料、金属等原料为主,不仅加剧了污染环境而且极大的增加了能源消耗。而且使用寿命缩短,造成了浪费。
第四,工业产品虽然方便快捷的被提供出来,但农民需要支付资金去购买,加重了生活负担。另外,虽然购买的产品属于个人私有,但其后续的使用、维修等活动并非完全自由的掌握,还需依赖外界,甚至要不停的花费资金去购买。
第五,工业产品的背后是技术的严格控制,很多产品的制作甚至包括产品形状等都被企业以专利的名义保护起来,技术被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农民获取技术的渠道变的狭小,获取技术的成本升高。
第六,工业产品以其获取方便、一次购买价格低等优势吞噬了传统制造法的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丧失了技术,也丧失了自由。
虽然这样对比,但绝不是期望我们回到过去,当然也回不去了,而是希望我们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智慧,更多的创造符合农民生产的工具,农业生产中我们应努力保留一些传统的生产方式。昨天去素攀布里府(音译KKF所在府)南侧的派特府(音译)参加一个传统农耕展,是一位拥有几十莱地的富家人,今年收获后请亲朋好友一起品尝各种自作食物举行的PARTY。中间一个表演环节就是靠几头牛不停的行走将收割的稻子碾压然后收获谷粒。男主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农民这样收获谷粒了,他想通过这种展示唤起人们对传统农业的重视。

以前我在中国北方一个农村工作时,想请村里最好的木匠做一个和我们收藏的传统马车一样的车轮,结果被告知:“只能作出个样子来,但不能使用”。想想我们身边还有多少东西已经被取代了。木质的叉子和藤编的椅子被铁叉和塑料椅取代,柳编的簸箕和草做的扫把被塑料、金属的代替,耕牛被换成了“铁牛”……消失的这些又到哪去了呢?
武侠小说中有句使用频率很高的话叫“剑在我在,剑亡我亡”,就是一个侠客会把他使用的宝剑视作自己的生命。虽然农民不会对农具有如此仗义的侠客精神,但被农民视为手脚的传统农具渐渐消失又意味着什么?
当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过去之时,随之而去的只有大众头脑中那短暂的记忆,而2009年的那些争论、怀疑、甚至诋毁却还在继续上演着。 新闻媒体也站在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位置上盘点着过去一年的热点新闻,而却很少有人盘点着农民几千年来的变化,农民失去了什么?又真正收获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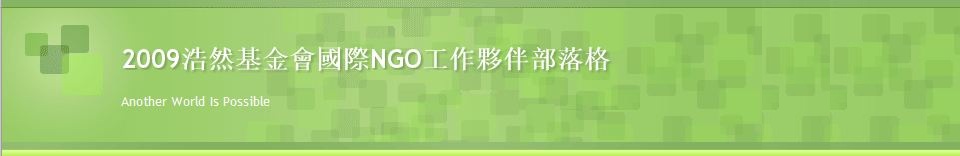


0 意見:
張貼留言